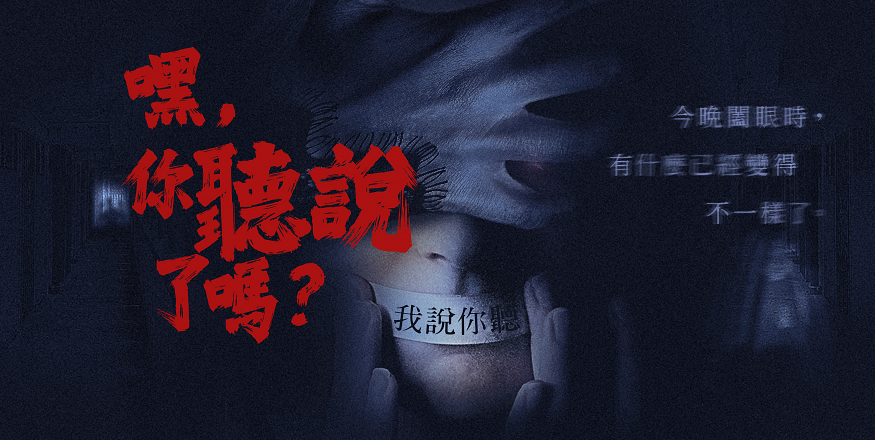未經授權者,不得將文章用於各種商業用途
「媽,這已經是這個月妳第三次為了這種事打電話給我......,不,我不是不願意幫忙,
而是妳要學著去接受爸過世這個事實…...好了!好了!我真的很忙,一會兒還要開會,
先不聊了!」我胡亂地掛上了電話,這種感覺特別的糟糕。
首先,我是一個受洗過的基督徒,雖然並不怎麼虔誠,也沒有去過幾次教會,只是因為老
婆信仰的關係,為了讓她高興,我也就一併受洗了。
父親已經過世了半年左右,在他過世以前大腦已經嚴重退化,家裡的人基本上都認不得了
,我不知道算不算幸運,我是他唯一叫得出名字的那一個。
父與子在東方社會一直以來就是一種畸形的關係,那是藤條、是拳頭、是擋了前方陽光的
肩膀、是人生選擇岔路上設下的重重關卡,十幾年來的爭吵,最終通向了沉默。
我和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好,或許大都數人都和我一樣,我們永遠成為不了那個理想中的乖
孩子,否則心理學就不會出現「未完成的願望之魔咒」這種像是二次元才會出現的可笑名
詞。
母親說,我是那時候他唯一認得的親人,所以我不得不去醫院,然後他會用瘦弱而乾枯的
手爪刮著我的手臂,說要我考上醫學院,那個十五年前,我沒能完成的他的夢想。
聽母親說,直到他臨終之前,都還在喊我的名字。
我一直以為身為人子的責任與義務,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就算是完滿了,誰知道
過世後,才是折磨人的開端。
母親說,由於父親是在北部過世的,火化之後讓我把他的骨灰帶回東部老家,然後不知道
她和哪一個師父討論,說因為父親晚年失智,恐怕靈魂不會跟著回來,便讓我一路開車回
來,沿途還要冒著被開罰單的風險撒冥紙,然後一邊喊父親叫他回家。
由於家裡就我一個獨子,所以也沒有其他人可以分擔這些亂七八糟的工作,我只好請了特
休,把骨灰綁在副駕,然後一路開了回去,下交流道以後,便把後車箱整袋的金紙扔在了
休息站,也算是功德圓滿了,仔細想想,這五個多小時,可能是我成年以後,和父親獨處
在一個空間最長的時間了吧!
父親整路是沉默的,要是他開口了,我想我會被嚇個半死!車子裡的氣氛很凝重,就好像
他真的坐在旁邊一樣,我不得不打開窗戶透透氣,想想也覺得挺好笑的,人好像活越久,
反而越活越回去,就說我母親吧!一個在那個年代能念到大學畢業的知識女性,到了老來
竟然迷信這些神啊、鬼的,有一陣子還差點被詐騙電話誆騙,對方和她說綁架了我,如果
不匯個一百萬,就等著收屍;當時她急得打給了我太太,和她再三確定我人在公司開會,
最荒謬的是她還不斷和我太太說,說對方有給她聽我的哭聲,哭聲?我連父親過世都沒流
過一滴眼淚,我太太還常開玩笑說,如果我會哭,那只會是鱷魚的眼淚。
後來母親才仔細回想,那個哭聲聽起來像是念國小、國中的孩子,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孩子
再幾年就要奔四十了!而父親呢?在他患上失智症之後,就更不用說了,所以我才說,人
真是越活越回去哪!
把父親的骨灰送回老家之後,母親的心還是沒有安定下來,就好像她根本不想結束整個喪
葬儀式一樣,好像還沒放下,就代表父親還沒有完全地離開人世,這幾天她不斷給我打電
話,挪!你看,十五通未接來電。
她一直吵嚷說父親沒有回老家,說甚麼師父跟她說魂魄掉在半路,問我是不是沒有沿途叫
他回家,興許是我不接電話,這幾天她同時也給我太太打電話,弄得我是身心俱疲。
「如果媽媽真的那麼在意的話,你就再走一趟吧!」太太不只一次和我這麼說。
「她老番顛,妳也跟著她一起起肖嗎?」我沒好氣地回了一句,太太也不敢再勸我。
那天晚上,我和太太用過了晚餐,到睡覺以前沒說過半句話,她明明知道我公事很忙了,
尤其這陣子有一筆大訂單要趕給客戶,下游的廠商還出了紕漏,都這個節骨眼了,還那這
種破事來煩我,想到這裡,又不禁來氣。
我轉過了身子,順手熄了小夜燈,腦子亂糟糟的。
那晚,我作了一個很真實的夢,我夢見自己正在開車,窗外的樹一棵一棵在我餘光閃過,
綠的褐的全連成了一片,像所有的色塊全暈在了一起,我揉了揉眼睛,右眼瞥見了副駕駛
突然坐了一個人。
那是一件連身的淡綠色病服,飄散著淡淡的消毒水混著尼古丁的氣味,他呆呆地看著窗外
的風景,那種厚重空氣凝結成塊的感覺,又塞了滿車。
就這樣開著、開著,他似乎正在數著甚麼,好像還哼了歌,五音不全的,但從來數不過十
,因為他忘了十以上的數字怎麼計算,所以又重頭來過。
我沒有打斷他,只是一直開呀開的,公路很順暢,只有少數幾台車子呼嘯,開長途車就是
這個樣子,很容易放空,等我回過神的時候,車內一片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而原本坐在副駕駛數數的父親,也不知去向。
我立刻把車子停在了路肩,然後跑下了車子,夢裡頭我不斷往回跑、往回喊著父親的名字
,不知道這樣跑了多久,太陽已經沒入了山巒,月亮高高掛在清冷的夜空中,沒有一片雲
朵。
就這樣走著、走著,等我意識到的時候,轉頭也也經看不見自己的車子,而腳下踩得也早
已不是甚麼水泥公路,而是一片泥巴地,舉目環顧,四周除了低矮的灌木叢再沒有其他,
空氣年黏稠稠的,像是食物要酸腐的溫度。
這條路不知道為什麼格外的熟悉,讓我想起了一個離家出走的男孩,他迷了路,在路邊又
餓、又累,委屈地蹲在角落啜泣,結局是他父親偉岸的身影牽起了他的手,大手拉著小手
,影子被月光拉得好長好長,那天,父親沒有責備他,只說了一句:「我們回家吧!」
想著想著,遠遠地,我終於看見一個人影,幽幽月光下,一個穿著病袍的男人蹲在了地上
,正數著地上的蝸牛,我緩緩踱了過去,他站了起來,衝著我傻笑,然後拉著我的手喊我
的名字。
「爸,我們回家吧!」我聽見自己顫抖地這麼喊著。
夢醒了,我從床上驚醒,驚動了一旁的太太,我趕緊擦乾了溽濕的眼角;天一亮,我和公
司告了假,給母親打了通電話,聽她叮囑了一堆神妖佛鬼的封建迷信,最後,我還是開著
車,沿著上一次的路途回了東部的老家,只是這一次開沒幾公里,我便大聲地喊著:「爸
,我們回家吧!」
這一次,車子內的氣氛沒有凍結,喊到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明明沒開窗子,雨水卻好像
濺到了臉上,溫熱溫熱的… …
https://reurl.cc/WrLxzO
--